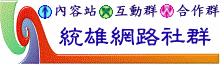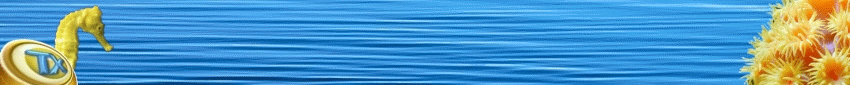
反抗爸爸的愛
發表刊物:臺大新潮 發表筆名:吳橋

|
爸爸 爸爸批改我的日記 爸爸冒名從軍記 博士論文獻詞 :獻給父親大人 悼亡父3帖 感謝爸爸和爺爺! A仔菜香: 吳倪根勤女士 紀念網站 |
爸爸是個軍人,所以是個腳踏實地的人。眼前的世界經由他保守而嚴肅的眼後,作一番綜合的分析,順著他的眼光,便可鋪出一條康莊、理想的大道。
爸爸在部隊裡,平均一個禮拜回家一次。在我年幼的時候,有好幾年的日子,寄居在親戚家,不然,就是長日伴隨著媽媽。爸爸強壯、高大、魁梧、結實。每當他低頭跨過那低矮的門,走進家裡時,我都偷偷地擠在媽媽的圍裙後面,怯生生地瞅著他。
那時,他很少對我發出直接的命令,除了每年三大節氣,祭祖的時候,他喊我過去,對祖宗牌位跪下,規規矩矩地磕三個響頭。
在舊日的相片上,我看見他把襁褓中的我,抱在膝上玩弄的鏡頭。滿足的笑靨,由他嘴角兩邊展開。可是,在我的記憶中,那太恍惚不可追了。
往後的日子裡爸爸繼續扮著嚴父的角色。而我在不能察覺的歲月中,一寸一寸的生長著。
初中畢業後,我竟然考進省中,當時還沒有國中,各校的升學率呈極不平均的差距。作為一個鄉下學校的畢業生,我還在沾沾自喜哩!
放榜後,一個暑熱的晚上,他把我叫到面前,開始我們第一次的長談。
他躺在涼席上,我搬把小矮凳坐在他旁邊,兩手絞在膝上。那晚的星星真多,繁空皓影,閃的我兩眼茫然。我一直不知道,經常沉浸在默然中的爸爸,卻始終關切地觀察著我,早為我在紛雜的社會中,規畫了一條飛騰的大路。
「附近的學風不大好,男孩子高中畢業以後,就蕩來蕩去無所事事。」他開場白道。的確,十幾年來,七、八個眷村,千餘戶人家,幾乎沒有人能打破不進大學的傳統。
又基於幹一行怨一行的心理吧,他繼續建立前提道:
「我也不要你進軍校,過當兵吃糧的苦日子,所以....」所以,他計畫讓我進台北一家工業公司,一所技士的養成班。
「學一門技術,」
「抱著一個鐵飯碗,」
「將來有資本,可以開大工廠....」
「這樣,至少可以騎馬找馬了!」
他欣慰的作了一個結論。
我,我不知道,星光太亮了。
不久,我就走入台北,跨進工廠。
像一尾剛從金魚缸裡拋進湖泊的魚,起初懷著顫驚,有點害羞,最後,卻開使自由自在的巡梭與呼吸。
在台北匆匆一待就是半年多,在三種基本技術工作中,我最得意的是車工,所有車床、沖床都玩熟了,可以作出各種圓軸、圓珠,甚至立面沖雕。作鉗工,雙手虎口被榔頭搥爛的痂,結了又爛,爛了又結。至於作鑄工,在翻砂階段卻始終翻不好,出模後要浪費更多整修的時間。
有一次在灌鐵漿的時候,一小朵火紅的鐵漿飛濺到我右手腕上,噗滋一聲輕響,我的皮膚立即就變成白煙,看見鮮紅的血管,在黑色燙焦的肌肉中跳動。
領班對我瞄了一眼,用下巴向門外點點,對我說:
「到大門口找阿巴桑,貼張沙隆巴斯。」
我向他鞠了一個躬、向外走。
他又把我叫住,再叮嚀:
「貼好,就要馬上回來喔!」
當時,留下了盃口大的痂痕;現在,則像士兵從戰場上帶回家的疤紋勳章。
在一個斜陽裹著冬風的傍晚,我快步的穿過植物園,兩手快樂地插在口袋裡,緊捏著這半年來,我賺得,溫暖的三百塊錢,正打算參觀民國五十八年,在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全國第一次書展。
人往往容易相信神奇的感召力量。突然,附近一所高中的校鐘響了,我順著那鐘聲迷人的招引望去。金色的陽光正映著建築物古老的磚紅,一群學生正緩步走出建國中學校門,雖然在同色的制服下,我看見一顆顆獨立的心,雖然在零亂的腳步中,我聽見一波波年輕的力。
我呢?
我,我這個躲在牆腳,縮在粗藍工作服中的瘦削身驅呀,難道就不配有奔放的活力嗎?不適合奔跑在那古舊的迴廊下嗎?不能憧憬獵取知識,作為登上更可以展望青天的階梯嗎?
我又想起讀書。
雖然在寒風裡,從我丹田產生了一股熱流,使我孤零而裸露的脖子也暖和了起來。就似乎有一粒被冷凍的種子,突然萌發了茁長的意志,我要走出陰影來,我要撕破上衣,長出肌肉來。
我自作主張離開了工廠,趕回家告訴父母我這個神妙的體悟。
或許,當時我還太小,太不懂如何婉轉地引導別人的善意,走向我所願的方向。我猝然間的改變,卻等於狠心地扯碎了爸爸精心繪製的藍圖。
在我意外出現的晚上,在我更意外的告白後,我愕然看見爸爸突然像彈丸般彈射起來,籐椅像被後座力拋飛的砲架,他高喊著:
「不行!不行!」
「去拿棍子來!」他對嚇呆了的弟弟怒喊。
「把行李扛回來!到街上紗廠做工去!」
「我就知道不能放你到台北!交壞朋友!」他對我絕望的喊。
他順手搶過叉晾衣竿的竹叉,兩指粗的竹竿太脆弱了,以致在我腿上裂成兩片,又裂成了四片。
這第一次的鞭苔,當竹杖斷裂時,像是也扯斷了他以尊親身份束縛我的繩索。
我靜靜的看著他的雙眼,我自由了。

我逃回台北,躲進斗室,拾起教科書。
我有4個月時間準備,而最怕的就是英文。因為打開國文、數學、理化、史地,都可以有一種「了解」。只有翻開英文書,完全不知所云。
真好,在公共垃圾箱裡一堆丟棄的廢紙中,我撿到一本英文法。
當我開始讀書,我才知道,過去我不是「讀不懂」書,而是根本沒讀書。
我逐漸領悟,學生的學習成就一半是自己努力的責任,另一半則是社會責任。而自己的責任部分中,又有一半是「知不知道可以努力、如何努力?」-也就是有沒有受到啟發的機會。
民國五十年代,城鄉的差距更大,我就學的鄉下初中,不少老師上課多半在罵校長、講閒話。有一位最「認真」的數學名師,我一整學年都沒有看見過他的鼻子。
上課鐘一響,他一定準時進教室,拎著一本參考書,就背對著我們,在黑板上抄題、解題;下課鐘一響,他把參考書一闔,頭一低就走了。一班小孩子在後面笑鬧、爭吵、翻窗子、用便當盒互相蓋頭。不論有什麼人聲、撞擊聲,老師處變不驚的持續抄題、解題,絕不回頭。這樣的小孩當然不會讀書、也無力升學。
我儲蓄的工資,剛好夠我在聯考前,每天吃三塊錢一碗的大碗麻醬麵,那時是以勞工為主職業的社會生態,大碗真的像花盆般的「大」,週末還可以多五毛加一碟海帶豆乾。
五月底,我在夜裡,搭火車悄悄回家,又偷偷把媽媽叫出來,向他要六十塊錢,好繳聯招的報名費。
當時她在作加工出口區的女紅,每天可以織一件繡花毛衣,每件工資2塊錢。
在圍牆外,她把錢塞給了我,她悲切看著我,我熱切望著她。
「媽,請給我一點鼓勵吧!使我能更有勇氣走向戰場!」
那天,是我第一次認識
什麼叫作「女人」?就是寵慣著兒子,但又永遠柔順著爸爸。她歪過了頭,輕輕說:
「我還是希望你聽爸爸的。」
可是,親情依然是永恆的恩情。
聯考第二天的第一堂,考數學。我因為沒有錶,每堂考試只有拚命快寫,大約早了二十分鐘便寫完了。理論上應該再作檢查,但當時年紀小,坐不住就出場了。
那是一棟木造舊樓,走下樓梯時,在寂靜的氛圍中,踩出「ㄍㄚ、ㄍㄚ」的聲音,在攔繩外、坐在操場上的家長們,紛紛轉過頭來張望。
迎面便看見爸爸,站著,左手著提著一瓶蘋果西打,右手搖著草帽,正東張西望。
笑容自我心底飛出來,一切怨言,如果曾經有,化作水流,化作風飄。
他費了好一番功夫,才輾轉打聽出我的考場。
我們上前拉拉手,愉快的我,在其他陪考者的詫異眼光下,咕嚕一口灌進西打,跳躍著再進去考理化。爸爸留下來,和別人談我的胃口好。

既然考進了建中,雖不如北一女有名,究竟尚差強人意,一切也就寧靜了。
事實上,爸爸仍時時刻刻為著我們身旁的環境在著想,前途、學業、將來的工作…甚至幫助擴展我們的人際關係。
記得有一次,弟弟學校裡開運動會,弟弟是童子軍,參加維持秩序。於是爸爸買了一大袋雪糕、餅乾,凡看見穿制服的,便發一份。
又有一次,他來建中找我。我到傳達室一看,他穿了一襲久從大陸上帶來,上好呢料,含背心、領結的深色大禮服,頭上還戴了一頂大禮帽。
在要求拜訪了訓導主任、訓育組長、教官…後,引他經過走廊的時,他還不斷地對下了課的老師們點頭微笑。居然有位年輕的女老師,被他嚇到了,匆匆溜下台階而去。
除了這些有趣的插曲,我們的意見也偶有不合,但都不如畢業後一次劇烈的爭執之甚。
三年中,我徹頭徹尾在念甲組,因為爸爸對熱門、冷門也略有所聞。
我猜,在他的心目中,在五十年的生活擔子壓迫後,他不再願他疼愛的子女,繼續扮演可能成為經濟弱者的角色。
可是,我一直在奇怪,主張爭取踏實的爸爸,為什麼會生下一個,時常會考慮人類如何創造歷史和組成社會的我,我想唸文科。
於是在投考大學時,我又悄悄調報名單報考乙組。
放榜的頭一天,公布甲組名單。一早我就溜上了山林,到了下午才想回家吃飯。回來的時候,碰見弟弟,說爸爸翻遍報紙,又借一份來看,然後面色難看的出去了。當時,別村裡是全鄉唯一錄取了逢甲的家門前,爆竹正成堆地,驕傲的鳴唱著。
第二天,因遲睡後遺的倦怠中,我被叫醒,說是考上台大。
媽媽出去買菜,爸爸在客聽低頭看書,弟弟溜不見了。
我覺得很無聊,就邀了隔壁的朋友,爬茶山聞杉樹。
此後的幾天,我動輒和爸爸爭著唸什麼科系有出息。
一直到我上成功嶺。
幾個月前,我收到爸爸一封信,興沖沖的告訴我,說是聽說醫科出路也不錯,我何妨轉個系?
那一陣子我很沉寂,為什麼?爸爸?我門有這麼親近深厚的名份,卻同時有這麼遙遠糢糊的認識?
爸爸,為什麼你自處如是淡泊,卻盼望我能享受奢華?為什麼你為國家犧牲了青春,卻不容我我為自己的理想奉獻?至少在這個園地裡,我找到了溫暖的窩,掘到了冽涼的泉,在我親手挪開的鵝卵石下,我栽下了或許能豐收的穀粒。
不過,爸爸並不對我失望,上次回家,他在書桌上抬起頭來,取下眼鏡,關了臺燈,誠懇的對我說:
「好好唸,」
「不要交些不三不四的女朋友,功課要緊。我會替你打聽,介紹一些名門閨秀給你,從前在大陸上,都是些望族。」
的確,近來,我很少回家了…
可是,哈!真,真不知道你信不信?…
我倒還懷念我和爸爸過去,那一段常常爭執,甚至彼此攻擊的日子。因為,因為至少我覺得,那還表示我們都還粗暴地要求對方的注意,渴求對方的關愛,而不是陌生的淡然。
前些晚,靠在床頭看書,突然,我想起爸爸,首先想起他那對眼睛。想起他那次打斷在我腿上的竹杖,想起當晚那顆失軌的流星。想起我們隔著牆互相嘔氣,想起他抱著我的那張兒提照片。
想起…想起第一次送我來台北時,他五十歲的肩,一邊扛著舖蓋,一邊扛隻大木箱,遲緩地踏上天橋,一級一級、一級一級…慢慢的爬。
他最先想培育的,最早要塑造的,第一個被他教育堅強的,竟首先站起來反抗他。
啊!我多麼希望,他肯從那護衛著他尊嚴的崗哨裡走出來,用他沉厚的手掌在我肩上一拍,說:
「來!我們去逛街、我們去賽跑,我們去看電影…。」
我有節奏地合上書,熄了燈,按熄了煙蒂,闔上了茶杯,往事便隨著這些節拍,像一節節的列車,拖過我的面前。
我放下身軀,枕住頭,望著逐漸增濃的黑夜,卻有東西來糢糊我的眼睛。我喃喃地對自己說:爸爸,我多麼希望你能夠聽到,我如何才能夠使你知道?
我吐出了一句,我一直很迫切,很想說的話:
「爸爸,我很愛你,爸爸…。」
後記
本文是我考上大學那一年,民六十二年冬所寫的感懷;民六十五年冬,發表在〈臺大新潮〉。
民七十九年,我以「資訊系統導入」的主題取得博士學位,在論文扉頁上,我寫下:
*
獻給
影響我靈魂最深處的父親
吳乾剛先生
飽經戰亂生死游離,您永遠樂觀;
渡過艱苦挫折坎坷,您永遠感激;
承受人生不平,您永遠謹守倫理進退;
面對物慾激盪,您永遠懷抱浪漫理想。
使我感念,
自己是多麼幸福。
*
我於民八十一年在世新大學創辦資訊管理系,後又受聘臺灣大學、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…等多所國內外大學,擔任資訊網路、數位文創、與計量方法學科的專任、兼任、客座、或講座。
從表面上看,似乎我人生換了跑道,回歸爸爸在二十年前為我規畫的路線。
我自己知道:我只是使用資訊與計量工具,持續探索我對人類行為與社會發展的好奇;自從爸爸讓我自由飛翔後,我的學習奔馳方向一以貫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