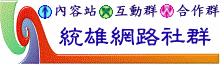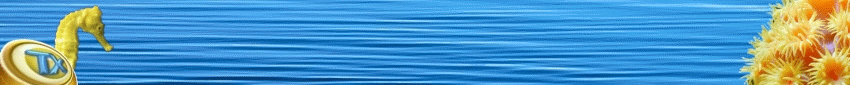
Birdie
〈臺大青年 77期, 1977〉
|
六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
今天下午五點,在松山搭上波音七四七,經日本,飛向美國。
飛機起飛前,落了一陣雨,起飛後,低頭俯瞰,只是灰蒼蒼的一片,別了,這塊曾經印證著我許多微薄的成就與挫折的土地。
自小就討厭送行,每一個握別,就像又把一雙溫暖的手,應生生推離自己的身邊,往往,感到的不是珍重的安慰,而是無情的拒斥。曾經因不肯送出國洽商的父親,遭到他帶有含蓄譴責的埋怨,但寧可驅策裝傻的情緒,來麻木自己的歉意,也不肯拗折自己,面對不願看見的場面。
相送到盡可能的遠,只像是促使無奈,延伸到盡可能的苦痛。
不願意送人,也婉謝了許多人的來送。但愈要在親密的人面前扭轉自己的背脊,似乎需要更大的勇氣。當我毫不反顧的大踏步走進出境室,逃避似地躲開了親友欲擁抱我的企圖,我真為自己突然擁有這種陌生的力量驚奇。
在座艙中,拿出大家送我的禮物,其中有一捲橋送給我的錄音帶,寫給我的曲和詩:
 別離
別離
演唱 演奏
演奏
是煙花?是霧紗?真別離?抑笑語?
才漸殘秋季,何來蕭索悲涼氣,誰問?
合歡雪,谷關夜,椰花晴,杜鵑蔭,
曾擬雙飛議,奈何關山險且阻,難渡!
嗯……嗯……
嗯……嗯……
愈近分手時,叨絮細語割不斷,難禁!
書一闕,夢一紙,有知人,要相記,
不記相聚少,卻記林深低語時,濃意!
孤翼薄,長征遠,今宵夜,誰能語?
異域鴃舌多,獨眠一掬情深處,誰顧?
嗯……嗯……
(相見時難別亦難,東風無力百花殘;)
嗯……嗯……
(此情可待成追憶,只是當時已惘然!)
愈近分手時,叨絮細語割不斷,難禁!
萬里情,一曲牽,慇勤意,已嘔盡!
雖然江海隔,同戴河漢鵲橋月,切常記!
要冷寒加衣!
(相見時難別亦難,東風無力百花殘;)
要風雨躲避!
(此情可待成追憶,只是當時已惘然!)
雖是庸俗語,一懷雜緒哽咽處,不能棄!
(相見時難別亦難,東風無力百花殘;)
(此情可待成追憶,只是當時已惘然!)
讀完後,不禁熱淚直流,高中後,便不曾再滴過一粒淚倔強的我!許多情景一幕幕重新又浮現眼前,現在,我離開了從困苦到小康到優裕的環境,離開了那些與男孩一爭短長的日子,離開了媽媽的嘮叨和爸爸對自己盲目的期望,放棄了對美麗的妹妹和狂放的弟弟的寵愛,以及,離開了,許多年來與許多朋友間不同感觸的友誼。
突然,我對自己的作法產生了極大的矛盾感,拼著一切去追求的東西,代價卻是如此的高。
再探首霾雲首,聰明的爸爸,當不會站在煙雨中,招呼他努力送走的女兒。可是,是否有那位癡傻的朋友,會在迎著雨絲,圍著鐵棘,孤寂的陽台上,向著看不見的我揮手呢?
別了,美麗的台灣,和關懷我的人們。
六十五年九月二日
今天己為到Berkeley後的第三天。
Berkeley以往大家把她譯做「柏克萊」,或「百克裡」,但直覺上我喜歡譯做「柏柯裡」,不僅聲音上更近似,也較有中國味兒,可以畀人想像的餘地。
柏柯裡是加州大學的分校之一,與哈佛在地理上一東一西,聲譽上卻是並駕齊驅。只不過東岸標榜的是傳統的績優與古老的氣息;而此間則迸發的是突破的進展,與新興的活力。
我來柏柯裡是繼續我在大學的研究,進入土木系衛生工程組的研究所,但我仍決意先到處參觀一番,以了解環境。
早上去了中文圖書館,規模很大,在Durant Hall內,其中收羅普及日文、韓文書籍史料,甚至有大量三十年代的作品及資料。又特去了在Banow
Hall地下室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圖書館,因主持人左傾,故里面陳設多為中共方面書報雜誌黨史等,佔地無前者大,陪我同去之學長催我快走,因台灣來的同學,多不屑在此多作逗留。另外又攀登了柏柯裡的標幟:Sather
Tower俯視舊金山海灣、金門大橋及所有的Campus,此塔三0七呎高,約合十層樓的高度。
來此三天,已知此地得天獨厚,氣候好又資源富,故一般人都很浪費,以用水及用紙最令我感到與台灣不同,紙製品隨用隨丟,而品質都為十分精良者。在校園裡到時間就澆草地,大片大片的用Sprinkler噴,流失蒸發量很大,此外,水龍頭流量也是又大又急。下午乘捷運系統在Bay
Area亂轉,但是都沒有下車,就好比坐公車遊覽市區般,看看美國城市,在公路、鐵路工程課上讀了那麼多捷運系統,現在才看到實況,我想台灣鐵路電氣化以後也就是如此了。
這裡吃的飯我簡直無法習慣,甜食甜得要死,而一般都是酸酸的發酵東西,有些蔬菜白煮在一起,那種味道實在奇怪,難吃!

 今天已有數位人認為我以前來過加州,因為他們說我有濃厚的California
accent,目前在I-House(國際學舍)的中國人我都已見到,他們自己生活在一圈,不與老美交談,所以英文其糟無比,勉強understandable,我打算明天與他們脫離,我看他們多數沒有勇氣走出圈子與老美做交誼上的來往。
今天已有數位人認為我以前來過加州,因為他們說我有濃厚的California
accent,目前在I-House(國際學舍)的中國人我都已見到,他們自己生活在一圈,不與老美交談,所以英文其糟無比,勉強understandable,我打算明天與他們脫離,我看他們多數沒有勇氣走出圈子與老美做交誼上的來往。
此地日本人很多,因他們政府對出國無限制,他們常第一年來唸英文,第二年才讀書,是很龐大的一股勢力。
走來走去都為新鮮感佔據著,並不想念家人,但一坐下休息,類似的景物都會將我帶回家園,因為這裡的風景氣候和溪頭、阿里山實在很像,真希望台灣的親友也能在此共享。
六十五年九月三日
今天吃晚飯與香港來的中國人同桌,他在此唸政治,從威斯康辛轉來,那是一所比柏柯裡更前進的學校,在一桌上,連老外都被他蓋倒,他長髮披頸,臉青面黑,散時特別說日後要與我談談,恐怖!
晚上校園搶劫強姦案層出不窮,因此不能出去?下午同系學長邀我去吃她女友的紅燒雞,看到他與同住者之種種,多為左派,第一次覺得有危險,還好他馬上就要搬,才放下心。
這裡太乾,皮膚都開始裂了。
六十五年七月七日
柏柯裡,不乏建築景觀上的特色,圍在校區四週的屋宇、屋頂都是由紅色的磚瓦砌成,從飛機上俯瞰,便可以發現,這似乎由格外寬厚的紅牆,所圈成的另一個天地。此點,是國內建築區的設計者,可以參考的。
幾天來,接觸了更多的留學生也鼓起勇氣和更多的老外談話,英文實在不行,只好有時比手劃腳。
老外會吃會玩,體力充足,讓我欽羨不已。
I-House人種很多,令人覺得有趣。不知如果我說:我覺得來對地方!是否為時尚早?但我一直喜歡具有開明氣氛而呈現多樣性的地方。
在台北,我有一些抱有「學院社會化」心態的朋友,相信他們一定會喜歡這裏。那時,我們常討論所謂真正的「社會化」!且以文學表現的形式為例吧!也並不如同某些人標榜的,迎合低知識份子的層面;而是懷著容忍與開放的胸襟,去了解、並關懷這社會上本存在的多樣、複雜的層面。
校中嬉皮式的音樂活動很盛,這裏的人彈起吉他,再連唱帶跳,味道真棒!在辦公大樓前的台階上可以自由表演,隨時都會有。
六十五年九月十六日
向學長借了一架錄音機,把橋的帶子聽了,著實令我唏噓不已。又接到台北朋友的來信,談到彼此在不同的環境中接受考驗與成長,不能相扶持,只能彼此鼓勵,一股無奈與熱氣自胸中起。拋開既有的有情,闖進新的人群,多少要感染拓荒者的畏懼,此時,過去的友誼,也發揮不少安慰的功效。
觀望一下此處中國留學生社交的情形,發覺女生的情況實在比較嚴重。獨來獨往的女生多;男生打單的也不少,但多半自視甚高。模樣兒並不可愛,似乎還秉持著高中生交異性朋友的觀念。這些人就是一直K書上來,不問世事的那批,但又到了適婚年齡,所以也是凡心大動,但是種種行徑又是非常可笑。他們佔據的優勢是至少可以藉名義回國省親,實際上討個老婆。女生則不然,據說第一、二年沒被追走,在此地位就會大降,我在參加他們活動時,看到幾個這種女孩子,外形、舉止都已有點老蒼,我想歲月及心靈的空虛,大概有相互蝕損的結果。值得嗎?這種令人寒顫的犧牲?
這裏中國人真多,到處都是,簡直不覺得自己在外國。
美國雖號稱民族大熔爐,實質上各民族還具相當個性,令我懷疑真正熔爐的可靠性。
六十五年九月十八日
今晚由學長的介紹到Walnut Creek一家中國人家去,那老中十年前來此唸衛工。今年所裏只有我和另一綽號「胖子」的中國人,兩人想知道衛工組的情形,故託人四處打聽,終於找到一個唸衛工的老中。
來此地唸土木的,都是進結構組,衛工已五年沒有中國人,而五年前唸的五個人,三個人只唸了Master,才兩個人唸P.H.D,而聽說論文都被刁難,不知為何會如此?這位楊學長一直強調P.H.D在柏柯裡有多難,他自己大概弄了八年,最後還是放棄了。他勸我們唸完Master後轉科,他承認柏柯裡的Master Program是全美最好的,但他認為此地的教授在你唸P.H.D時,他們的前題是你應該有完全獨立做學問的能力,一切實驗都是自己從基礎做起,沒有較低level的助手幫忙,指導老師沒有「你是我學生,我一定庇護你走出校門」的觀念。聽起來,一方面學生自己很累,但多方面我到覺得頗有挑戰性。他又說:十年前柏柯裡的衛工組確是獨霸天下,但現在三大巨頭之二,已於前年相繼去世,耆老只剩一人在獨撐大樑,其他兩位年資較淺者又是個性古怪,對爭取校外Project,中興系譽並不熱衷,再加上現在污染,環境保護又是熱門話題,別的學校一個個相繼設立衛工系,都是幹勁十足,柏柯裡就沒那麼突出。
綜觀他的話,我承認衛工界的後起之秀都是潛力極大,柏柯裡此刻也許並不若當初一枝獨秀,但也不是一流之外。這位學長如此沮喪我們,說了那麼多negative的話,是否與他當初的英文表達能力(對留學生太重要了!),他的社交力,與教授相處自己主動與否?等等背景都有關?不免在我心中打了一個大問號。
我回來後,雖一度覺得懊喪,為什麼這條路如是艱鉅!但想想並不可全信,開學後好好觀察,了解系裏的情形是最重要的。苦,我不畏懼,最怕沒有經濟支柱。
六十五年九月十九日
今天認識一個男孩方傑,是從前台視劇場「小蕙與丁丁」的童星,人很爽,很會開玩笑,喜歡唱歌,自己做了幾首中文歌,這點與橋認為「要有中國的音樂,首先要使中國的舌頭唱中國歌才行!」觀點一致。
不過,方傑的歌有濃厚「劉家班」的味道是唯一的遺憾。
六十五年十月三日
這學期開學,我每天都得讀到子夜一點,還是跟不上。reading
assignment太多,唸的速度太慢,最重要的是有一科「應用生態學」教授是英國人,我根本聽不懂他在講什麼,很痛苦。其他三科還好,可懂百分之八十。
努力了一個星期,到星期五真希望澈底的休息。週末恰有右派學生會舉辦的迎新會,電影加party,電影是楓葉情,菜!這邊舞會都是現場band,跳起來較過癮,並且也是太久沒這機會,大家下場的都很踴躍。
我現在心情又很痛苦,主要是學業上的壓力,上課聽不懂,書唸不完,美國學生好像很通的樣子。我們班上共三十五人,五個女生,東方人約有五、六位。此地weekdays真是工作至極,weekend也真是享樂至極,老美皆如是,但我們可沒福氣我每天到系裡study
room去唸書,晚上從校園走出來已十二點多,在路上看到從圖書館出來匆匆回去的學生,都是東方人,星期日到校區唸書的也是老中。我想像的出:這裏的生活日後會很苦悶,很掙扎的,假如學業上出問題的話。每天都很努力,又很單調,床是我現在最盼望的地方,我勸自己要看開點,否則必然無法活下去。
六十五年十月十四日
 看了一場披頭四演唱歷史的紀錄片,初期,他們的颱風好,給人溫暖的感覺,但後來抽大麻煙之後,就不太可愛了。好像一個人的生命,剛開始最純,最可愛,越到後,越複雜,也難以令人有直覺衝動式的贊同了。
看了一場披頭四演唱歷史的紀錄片,初期,他們的颱風好,給人溫暖的感覺,但後來抽大麻煙之後,就不太可愛了。好像一個人的生命,剛開始最純,最可愛,越到後,越複雜,也難以令人有直覺衝動式的贊同了。
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
這裡的女孩,和我同屆的,與我熟悉的幾位都和男朋友分開,每天通電話、寫信,還是很苦惱,抱著枕頭飲泣。他們很奇怪為什麼我仍是笑嘻嘻的,每天很愉快?我想我complain也沒用,還不如每天很愉快的樣子,自己求得解決之道,覺得很有趣的活著。
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
十一月五日,爸爸從Wisconsin來,正好我的mid term exam考完,陪他玩了三天。
 這裡出題目很有內容,決不是故意要殺你,只是看你了解的程度如何,最重要的還是注重思考能力,過了一個mid
term,我的兩頰都瘦下去了。還有三個星期,本quarter就結束,二十一日I-House有Thanksgiving
formal dance,想起萬聖節的化裝舞會,看到老美個個化妝的奇形怪狀,覺得是一個funny的節目,但thanksgiving 就不同了,是一個非常正式的節日。
這裡出題目很有內容,決不是故意要殺你,只是看你了解的程度如何,最重要的還是注重思考能力,過了一個mid
term,我的兩頰都瘦下去了。還有三個星期,本quarter就結束,二十一日I-House有Thanksgiving
formal dance,想起萬聖節的化裝舞會,看到老美個個化妝的奇形怪狀,覺得是一個funny的節目,但thanksgiving 就不同了,是一個非常正式的節日。
在此地真是度日如飛,時間單位根本是以星期計,這就是在高度緊張的生活下情形,甚至家書都懶得寫。
六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氣象報告,全美各地都在下雪,而加州仍是天空晴朗,一片蔚藍,除了早晨有時下霧外,白天只是在空氣中加了幾分嗅覺上的冷凝。
剛開學時,我的態度還算比較放得開,還能讓自己去游泳,與老美交際,但在期中考後,作業多得令人透不過氣來,別說游泳,在飯桌上都是浪費時間。或許是對時間的安排還不理想,因此不覺得遊刃有餘。
六十五年十二月四日
學期終於結束了,昨天已考完二科,剩下的在下星期。
上週感恩節放假四天,我開了兩天夜車,做了Water Quality
Management三個習題,完工時已是假期結束後星期一的凌晨四點。略加收拾,便又匆匆趕去上課,因為授課時間不夠,教授甚至在早上七點就加課。現在總算考過了,所得的感覺,除了學問上略有所獲外,就是「滄桑」兩字。
Quarter Break 我仍我然停在Ihouse,我想去L.A.(洛山磯)走一走,假如經濟能力允許的話。我們放假二十一天,一月六日開學。
六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
昨天去見了Advisor,決定下學期所選的課,五門。冬季班的課程,將是這一年所學的靈魂。Advisor說我doing very well,他不知道我在上課聽不懂時種種的情緒壓力,他只是看了我的成績:三個A,一個B,平均有三、六分,合乎P.H.D學位要求的平均成績-三、五分。

寒假三個月M我和I-House其他九位新生租了兩部七十六年的道奇車,同往南行;先沿加州海岸至Hearst
Castle,此Hearst family的私屋,為一十八世紀的保壘,內部奢華,現已捐給加州政府,這種觀念也是國內辦觀光事業者可以參考的。再經過(死亡谷國家公園),景觀壯麗,變化無窮。往Las
Vagas,看了一場topless show,是巴黎麗都的表演,又玩了吃角子老虎,贏了二十元。之後又去聖地牙哥,玩了Sea
world,匆匆趕至L.A.。
 此行共開車1400 miles,除了晚上上館子吃的較好,我們自己帶麵包及罐頭,晚上擠Metel,故花費並不多。沿途經過的大大小小城市比較一番,我還是最喜歡Bay
Area(指舊金山地區,因是一個大海而得名)尤其是柏柯裡,天空永遠是蔚藍的,乾淨的,不若許多城市,在郊區還算清朗,越進市內,天空越變向灰色,污染情況令人不舒服,但整體上還是比台北好,大概習慣柏柯裡的清潔後,就不免使人吹毛求疵。一路上的感覺是美國的公路修得真好,我看他們運輸的基本動力是公路,無孔不入,又覺得資本主義下的個人主義在美國已發展到極限了,太浪費汽油。
此行共開車1400 miles,除了晚上上館子吃的較好,我們自己帶麵包及罐頭,晚上擠Metel,故花費並不多。沿途經過的大大小小城市比較一番,我還是最喜歡Bay
Area(指舊金山地區,因是一個大海而得名)尤其是柏柯裡,天空永遠是蔚藍的,乾淨的,不若許多城市,在郊區還算清朗,越進市內,天空越變向灰色,污染情況令人不舒服,但整體上還是比台北好,大概習慣柏柯裡的清潔後,就不免使人吹毛求疵。一路上的感覺是美國的公路修得真好,我看他們運輸的基本動力是公路,無孔不入,又覺得資本主義下的個人主義在美國已發展到極限了,太浪費汽油。
六十六年一月七日
最近尤其感到青春之易逝,好時光不再,許多美好的東西彈指功夫就消逝了。整天關起來讀書,對人生最好的年歲是很殘酷的事。Enjoy life while you can!這是加州的好天氣,給我最大的啟示。
寫給台青的稿件,已大致就緒。
六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
我們剛考完,我又活過來了,第一件事是游泳去!
昨天系裡舉行Cocktail party
第一次有機會與全班同學聊聊得知下個quarter最是辛苦,連同老美都覺得不容易過,想想也只好苦撐了。
衛工組班上有兩三個老美女友都是中國人,其中一對還living
together,酒會時,他們都把另一半帶去,看那情形,這種事也許只有舊金山才有,這裡的人種族歧視弱的多。
昨天開始I-House沒飯吃了,寒假停火。我買了一個電鍋,還有生力麵、罐頭、打算自力更生,到外面吃太累、太花錢。在San
Francisco
的好處,就是處都是中國東西,根本不會有在異域之感,尤其吃的,什麼都有,譬如今天中午,我吃了芝麻蘿蔔絲及豆沙餡餅,燒餅油條。
美國同學多已返鄉或渡假去也,留此地的多為外國學生,X'mas的味道並不十分顯著。
到美三個月,在期末考時,我才真正突然地想起家來,也許是讀書壓力太大了吧!
六十六年二月十六日
想不到在我的四周會掀起一陣小小的漣漪,我得到兩個老中求婚性質的表白。班上老美也請我出去跳舞,並且有一印度人對我頻頻試探。在I-House中,隱約也察覺到有人虎視眈眈。我從來沒感覺到我有這麼大的魅力過,當然是又得意又不免煩惱。據說,我現在是變好看了許多,但是歸根結底一句話,我知道這乃是因為柏柯裡是個男大多於女的地方,尤其是I-House,更是女孩太少。這裡老中想結婚的很多,物質條件好的也不少,但就是不對頭,我看大家都在試來試去,很無聊。
這種事該來就來,急也沒用,不過他們的方式相當單刀直入,決不浪費彼此時間。還有個感觸:以前在班上,大家待我如小男生,好像沒有性別差異,但現在碰到的人,不管是老美或老中,有意無意會讓人覺得他們欣賞你,也許是這些人年紀都比較大吧,因此之故,我更需要behave
myself。
近幾天特別溫暖,許多櫻花及大樹突然都佈滿了碎花或抽出了滿枝嫩芽,春天的氣息散佈在空氣中。
早晨,在步向教室的途中,在一幅柔風搖翠的景致裹覆下,似乎有不知名的力量,來托負我書本的沉甸,鬆弛我腳步的匆忙,促我反顧這一個多學期來的總總。
在人際上,我和班上的人愈趨熟稔,與中國人反倒疏遠了。我覺得與老美相處似乎倒自然,許多中國人忌諱多,大概在國內求學階段,與現實隔離,心境不夠廣闊,有時實在不能忍受。不過,老美又太獨立了,很難與他們真正交朋友,除非有共同實利上的目的。在I-House的團體生活中,發現了我個人不少的缺點,我想是土木系四年師長親友都太縱容我了,以致養成惡習,需要努力去改。
在學業上,生活經驗上,充分感到頭腦的重要性:要知道自己在幹什麼!我在心態上還不時把自己看成小孩子,但逐漸的,我發覺this
no way!在這裡講究(競爭),誰的態度成熟,想的透徹,腦筋冷靜,誰才會勝利!
陌生的環境,可以廣闊胸臆;獨立生活,使我學習養育自己。
 後記
後記
寫本篇文字,我並不是想把它當作一篇遊記,更非僅是花絮式的報導。
我來美的時間不長,體驗還嫌不夠深刻,也不善役用文字,當然不能寫「留學必讀」或「美國研究」等等的理論。但我把所看到,所聽到,所談到的許多小事件,依然懇切地獻給有心來美的人,作一個小小的參酌。
赴美而有成就,與進一步,更有理想的人固然多。但最怕是觀念錯誤,語文能力不夠,胸襟不夠開放,與人交往不自然,便根本無法吸收美國文化的最精粹處。像這種人,來了又不能回國,惟以淒慘的事實破滅台灣家人的幻想,否定了「吾子在美」的虛榮,終於淹沒在異族的恥笑中。
我,和我所敬佩的留學生一樣,對自己的期許是:既然家鄉已隔離在太平洋之彼岸,我就要盡力打入此地的社會,但當飽足了我所欠缺的一切,我又要回到那與我皮膚一樣顏色的土地,我才能找到落實的發展,付出真正的貢獻。
有一天,我又要飛回家,飛回那塊曾經印證著我許多微薄的成就與挫折的土地。我會快樂的伸出雙手,面對迎接我的人。
那一刻,我才能肯定自己東飛的代價。
在青雲之上,我會低頭俯瞰,輕輕呼喚:
「我回來了,美麗的台灣,和關懷我的人們!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