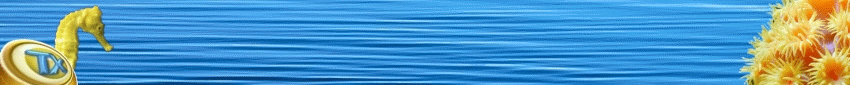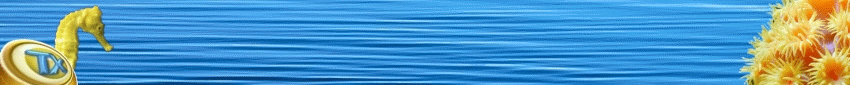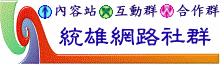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,臺灣第一次絕食靜坐的學運,可能是發生在1971年臺大校園內的傅鐘下、杜鵑花旁。
當時適逢釣魚臺事件,突然引爆了巨量的自由言論,多樣化-或可說是內容蕪雜的大字報,貼滿了校園大道兩旁的每棵椰子樹,這樣的奇景,是其後數十年也沒有再見到過的。但是,那時傳播相對不發達,媒體很有限,更受威權體制控管,活動的訊息整個被封鎖在校牆內,外界很少知道,更無從關懷。
我當時還是建國高中的學生,因為內定接任校刊的總編輯,經由學生編務與思想交流的管道,也受邀到臺大開了一場座談會。會中有些學生主張,為了打破社會的冷漠,必須採取更激進的手段:絕食靜坐。
等我後來就讀臺大,我的學長-現在臺大任教的魏教授告訴我,教官聽說絕食靜坐的風聲,就召集了包括他在內的一批親執政黨學生,指點他們:每當靜坐學生號召人群的時候,混在人潮中一起聚攏,但當學運學生站起來要講演訴求的時候,就同時帶著嗤之以鼻的神色,搖著頭向四面八方掉頭散去,其他的學生也就不由自主的跟著走了。這一招果然很有用,人潮的聚散,一鼓作氣、再而衰、三而竭。絕食的學生到晚間竟然只剩下個位數,撐不了幾天已經體力透支,校警乘著半夜把他們
抬到醫院,煙消雲散。
不過,當時曾經聲援的學生教師不少在後來都遭受干擾,甚至有老師被解聘。我回到學校也被教官叫去面斥「在外串連、有損校譽」,並解除了我的總編輯職務。連我這種外圍參與者,也難逃遭受整肅。
對照近日黨政要員,或主動、或默許應用各種資源、經由各種管道對中正堂靜坐學生展開反制,執政者對學運的仇視與綿密的打擊,真是始終沒有改變啊!
杜鵑花學運的主軸,就是高懸在傅鐘旁的一付對聯:「風聲、雨聲、讀書聲、聲聲入耳;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、事事關心。」初看好像很抽像,其實脈絡分明。「國事、天下事」指的是保釣、民主自由、民族主義論戰。「家事」也很多,其中重心之一是「反髮禁」。
當時美國隨著民權運動興起,蓄髮成為一種主張民權的象徵。但臺灣的執政者卻將髮禁作為鉗制思想自由、辨識順民的標誌,同時和「公序良俗、品行端正」綁在一起。這一代的年輕人,可能根本想不到,在街頭隨時會碰到一個便衣警察,突然一把揪住你的領子,把你推到路邊,用剪刀隨便把你的頭髮剪幾刀。
也許有人會說,這麼瑣碎的事,怎麼也能成為訴求?其實是因為學生不能夠「反公序良俗」,只能夠「反髮禁」,真正反的則是粉飾著「公序良俗」、卻包裹著壓制民權的政治符號。
現在也有人說,這次學運的訴求不具體。經歷過杜鵑花學運的我,一看他們「要求藍綠道歉」「要求族群平等法」的主張,就非常明白,他們真正反的是粉飾著愛鄉愛土、卻包裹著動員民粹的政治符號。
政治的爭議有三類,第一是屬於公共政策,如「核四」的爭議,這種衝突的激情較小;第二是屬於制度的,如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「國會改革」之爭,衝突拖延較長;牽連最廣的就是民族認同之爭,從對手的「出生」否定掉對手的一切。今日許多國家地區仍在承受這種衝突的災難:東歐、中亞、盧安達,連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的北愛也不能倖免。
這次選舉後大家的心理創傷,有幾分是為了「核四」?「國會改革」?還不是為了過度的族群動員!幸而,臺灣絕大多數的人民事實上是同一種族,產生的只是假性的、炒作的、為了政治權力的族群動員,所以才沒有前述區域的流血慘劇,但情緒上的打擊與撕裂已受傷極深。
更悲哀的是「沉默螺旋現象」,也就是一個政治符號被賦與至高無上的價值以後,可以用愛與融合的外衣,包裹著仇恨與民粹動員,卻愈來愈沒有人敢說破。
隨著「螺旋」的擴大,自認屬於「政治符號正確」色彩鮮明的個人、組織、媒體可以更赤裸裸的號召民粹,譬如某政黨大報的競選廣告,可以理直氣壯的宣稱,這次大選是「臺灣人」對抗「中國人」,而在「臺灣人」下以大字加註:「河洛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」;而而在「中國人」下大字加註:「浙江人、廣東人、湖南人…(其他大陸各省)…國民黨、共產黨」。
而自居於中道的一方,深怕被戴帽子,於是噤聲、撇清;實在要說話的時候,就作一些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表述,或是小心翼翼、作一些扭扭捏捏的規勸與建言。(這樣的人,大概包括我自己在內吧!)
學運之可愛,就在於學生敢於不沉默,要求主事者道歉。學生提出的其他相關訴求,其實都是衍生事件。真正的核心就是:族群動員對選舉確實有效,但是對激生的全民焦慮與衝突,主事者能沒有道德責任嗎?
當前臺灣的主要族群間,其實並沒有法律上不平等的問題,而是被政治操作撕裂,但學生不能挑戰民粹政治符號,只好被迫拐彎在「法」上求平等,正如同當年的杜鵑花學運,被迫拐彎在「髮」上求民權。
這次最令人驚奇的發展,是部分1990年野百合學運人士對這次學運的撻伐與輕賤。學運參與者對自己可能有不同的定位,杜鵑花學運中的學生,期望自己是被解放的一員,是人民之一,最後並沒有任何一人投身政治實務。從結果論,上次野百合學運中不少人士,似乎是追求擔任「解放者」,有許多人正擔任著黨政要職。當這些黨政官員公開懷疑學生是政黨在「利用學生」的時候,是否等同自承他們今日的黨政地位,就是「利用學運」的結果呢?身為學運的受益者,卻對學運冷嘲熱諷,不論動機為何,總是有點奇怪的感覺。
1990的野百合正盛開在廟堂之上,有再追求進步的能力與責任,也要有抗拒權力誘惑的定力;2004年第二次野百合學運的幼苗,在中正堂旁正被快速的遺忘中,使我想起,三十多年前那一叢凋零的杜鵑。
<回本期目錄>
《政大社科院政策論壇》第一百零九號 2004.04.23 發行